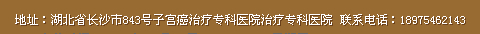学了那么久英语,却发现连菜单都看不懂,原
学了无数年英语,在英语国家也生活了9年多了,却发现英语词汇真是永远学不完,平时阅读报纸评论和网上论坛,依然经常有不认识的词汇,虽然不影响理解,但总觉得不爽。这不是我词汇太少,而纯粹是英语词汇“变态”的多。德语词汇量最大的杜登大辞典收有大概20万词汇,现代西班牙词汇仅有23万,法语更少,只有10万左右,立志于维护法语纯洁性的法兰西学院仅仅承认其中的多个;而英语现代词汇估计已经突破了万。当然这万不可能都是常用词,但足可见英语词汇之浩大,从而解释了为什么现实中似乎有学不完的生词,而且很多都是一般人都会的词汇。
这让我想到汉语跟英语相比的简练。普通人只要学会汉字就可以基本读书看报。有人会说,那只是字啊,跟词汇不同,这正是我想说的,汉语构词法的魅力和高超。汉语构词以灵活简单著称,创造性的组合为数不多的汉字表达出无数种含义,而与此相比,英语的顽疾就是出现一个新事物,往往就要为其造一个词,而这个词往往跟任何已有词汇没有关联,哪怕在意思上很近。
简单的例子,表示动物的词汇,汉语里有简单的“豹”,详细的分类,我们有猎豹、花豹、美洲豹。只要你知道了“豹”是一种猛兽,就可以知道猎豹花豹金钱豹大致是什么东西,哪怕是第一次看见,而且猎、花、美洲都是有具体含义的。
在英语里,像对应的是:cheetah,leopard,cougar。三者之间毫无关联,你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没语境也不可能猜出。英语还生怕这太简单,cougar也可以叫puma,或者panther。汉语有马,于是造出斑马,河马,角马,英语zebra,hippopotamus,wilderbeest(注意不是beast),如何看出这些是四脚动物而不是花草或者家具?英语变态到同样的动物公母还有分两个完全毫无关系的词,比如Rooster(公鸡),hen(母鸡,但又不仅指母鸡),统称chicken;牛更复杂,统称cattle,公牛叫bull,但阉割过的公牛叫ox,我们经常以为母牛就是cow,其实cow仅指已经生了小牛的母牛,年轻未产自的母牛还有专门名字heifer,而小牛又叫calf,只见看起来毫无关联。
说到calf,我看动物世界就发现小象也叫calf,幼年鲸鱼也叫calf,里面并没有特别共同之处,但不是所有哺乳动物都能叫calf,小狗叫puppy,小鹿叫fawn(公鹿母鹿分别叫deer和doe),狮子老虎的幼崽叫cub,马和斑马的幼崽叫foal。我又糊涂了,既然你觉得马和斑马是一类,为什么horse和zebra啥关系都没有?耍我?我一直以为pony是指小马,结果pony是指成年的小型马,而不是小时候的马。这些都是今天才知道的,不是动物学家,谁分得清啊?
还有鱼类。这个更可怕。汉语里都是以鱼结尾,英语就除了catfish等少数就都各展风采了,什么trout(鳟鱼)、cod(鳕鱼)、mackerel(鲭鱼)、carp(鲤鱼)、tuna(金枪鱼)、salmon(鲑鱼)、bass(海鲈鱼)、grouper(石斑鱼)、(比目鱼)、perch(鲈鱼),当然鱼太多不可能一看就知道哪类,但起码让人点菜的时候知道是水里游的不是天上飞的吧?提到点菜,有次在华盛顿看到venison,想来想去面熟但又记不得,经提醒是鹿肉——请问跟鹿有毛关系?
表示水果的词汇。“果”我们知道是果实,所以我们有苹果、芒果、无花果,英语里照样是三个毫无关联的词apple,mango,fig;我们有桃、杨桃、水蜜桃、猕猴桃,英语里又是一堆毫无关联的词汇,比如kiwi是个什么玩意儿,跟水果有神马关系?汉语还有各种瓜,西瓜、冬瓜、木瓜、丝瓜、黄瓜、青瓜、南瓜、苦瓜、哈密瓜等等,即使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也知道是个瓜果类食物,英语里又是一堆新词(虽然个别有melon在里面)。当然英语也有稍微讲理的时候,比如蓝莓、草莓、黑莓就跟汉语造词类似,但结果就是这些词都很长。
再看衣服。汉语表示衣服的基本词汇是“衣”“衫”“服”数字,于是衍生出衬衣、内衣、毛衣、风衣、睡衣、大衣、雨衣、羽绒服、西服、圆领衫、T恤衫;英语里则毫无系统性,比如coat,shirt,underwear,sweater,pajama,suit,polo等等。cardigan就是前面有纽扣的毛衣,blazer其实就是休闲西服,但两个词与sweater,suit毫无关联。中国人常穿的秋裤,一听就知道是天冷下来穿的裤子,英语里叫longJohns,完全不知所云。parka是冬天穿的带帽子和毛领子的羽绒服,不知道的还以为跟公园有关系。
最让人抓狂的是病的名字。在英语里,似乎你得有个很好的教育才能熟练知道很多常见的疾病怎么说,就炎症而言,它里面的一堆-itis简直吓人,hepatitis,bronchitis,arthritis,rhinitis这些算常见的,显然汉语里的肝炎、气管炎、关节炎、鼻炎要友好很多,连文盲老太都知道,不需要了解那么多拉丁词根。不常见的还有karatitis(角膜炎)、mastitis(乳腺炎),enteritis(肠炎)知道的人肯定就少很多。但肺炎明明是肺部炎症,人家叫pneumonia。另外猜猜paronychia,鬼才知道,原来是我曾经得过的“甲沟炎”。如果医生告诉一个美国人你得了paronychia,不知道百分之几的人明白到底是哪里有病了。医生职业里面我们汉语有很容易理解的儿科医生、妇科医生、产科医生、皮肤科医生、眼科医生、牙科医生、英语又是一堆拉丁词根:pediatrician,gynecologist,obstetrician,dermatologist,ophthalmologist,dentist连结尾都不一样。
再来几个粗俗的。鼻屎、耳屎,都通俗易懂,英语里要区别对待,鼻屎叫booger,耳屎叫earwax,至于眼屎则没有固定的说法,叫eyegum(gum不是口香糖吗,用一个词恶心不恶心)。这些词也可以统一成nasalmucus,eyemucus,earmucus,但听起来已经是医学用语了。
总之英语词汇貌似浩瀚庞大,但很大程度是因为它不够灵活的造词法,导致不停得创造新词给各种事物命名,而完全忽略其间的关联。最简单的,我们汉语有了“桌”一词,就衍生出书桌,英语非要搞个desk,完全不顾它其实就是table的一种。我们汉语有了“杯”一词,就衍生出茶杯、酒杯、玻璃杯,英语里的cup和glass还是看不出用途上的任何关系。另外goblet是什么?原来是“高脚杯”,另外还有专门用途的比如mug,其实不就是有个把的瓷杯子?还有一个奇特的tumbler,专指平底的玻璃杯,这不是吃饱了撑着吗?这也许也体现了中国人和西方人在理解世界方式上的区别。
为什么英语就不能多用一些言简意赅的复合词呢?因为它做不到,西方语言表音,除了其少数的词根,大多字母或字母组合并没有任何实际的含义。而汉字的简洁简直无人能比,因为它的每个单音节字承载的信息量比西方语言的一个甚至多个音节英语要多得多。英语如若像汉语那么大规模用复合词,估计就会像德语一样动不动出现一些15个字母以上的怪物了。语言学家调查表明,在世界主要语言里面,要表达同样的意思,汉语的音节最短,最长的则是日语、意大利、西班牙这些构词能力极弱的语言。结果是,表达同样的意思,说普通话者语速最慢,而日本人、意大利人语速最快,因为他要在类似时间内说出两倍甚至三倍于汉语的音节。麦当劳在汉语里三个音节,在日语里则是ma-ku-do-na-ru-do。
说到最后,其实意思是想强调汉语的巨大魅力,其强大的词汇组合再生能力和难以比美的精炼度。如今中国的年轻人热衷学英语,向往走向世界,当然是好事,但是无论生活在何处,无论觉得西方如今有多先进,千万别忘了,自己母语的精妙其实是任何其他语言难以媲美的。
转载请注明:http://www.kdghb.com/hbyx/5855.html